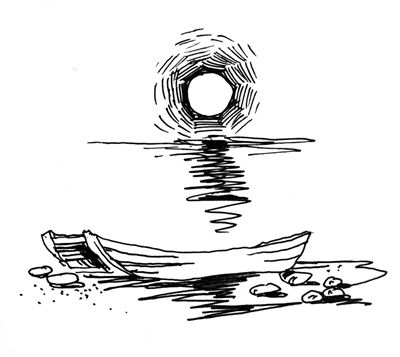桃花就要开落了,大头儿说:“开秤!”
二头儿将手探进草垛子,好次便有了定论。若是王爷地草,他就要折下一截,口里咂一下了,区别上、下王爷地草。上王爷地草是极品,就要请卖家喝茶了。茶不仅仅是喝茶,吃完点心,请到水坊泡过,伺候的舒舒服服了,便要摸牙子了。摸牙子就是探价,双方就要有几个回合。谈拢了,就放码子。码子就是底价,不论秋后价格如何,不能低于这个价,这是上王爷地草独有的待遇。草市有个规矩,起运时开价,平时收草,记账上即认了“生死簿”。
草头儿收完草,秤一放起来,掏草工就要丈锹。丈锹是行话,一般的掏草工多是穷苦劳力,掏草用的工具便由草场提供。掏草的铁锹是特制的,锹头窄而长。丈锹就是查验一下工具,若有损坏,就要修一修,或换一把。其实这是草场掌握掏草工的一个勾当,也就知道了掏草工的去留了。
识草苗是掏草工的一个本领,草苗四五枝生,便有老相,下锹就要一尺见外。掏草不能伤草。掏草有个规矩:斩草留根。不能将根子掏死。草场收草,不收“串子”,只收“栽子”。如果一年里掏草工有两次掏“串子”的记录,这碗黄连饭就吃不成了。本意上是为保护草场资源。简单说“串子”就是正在生长的草,匍匐在地,便有了这个形象称谓。“栽子”是熟草,直扎地下,粗壮孔武,与地面垂直,故名。掏草工背地里叫“二掌柜”。这是个双语,明里是说好草,暗里是贬低谩骂“二头儿”,也叫裤裆棒棒,交完草入了库后,又叫割毬货。掏草工最恨的就是二头儿。压质压价,剋扣斤两是二头儿和草头的本领,掏草工背后有一句顺口溜:“二头儿先死,草头割毬!”因此,后来人又说:“山野草场,没什么好瓷(词)”
王蕊在黄河达拉滩边掏草,实在没什么宿处,就掏了个地窨子容身。十几年后,“雁行”规矩打破,王蕊就在黄河边上安了一口锅,称为伙盘地,以此发家,直至有了二十间大碾房,被人称为西碾房,渐积人气,成了一个村,招来不少掏草工,西碾房又成了草场名。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西碾房一场独大,成了垄断一方的甘草行大商号。有“王家不到河口,草价不开市”的说法。
这一年,西碾房和荣升昌争霸,河口草市迟迟开不了价,甘草积在草店和码头。公义昌瞅准这个机会,引进隆美洋行资金,大肆收购,草市出现混乱,大量“串子”草充斥市场,隆美洋行照收不误,以致以后二年草场歉收甚至绝收。只有公义昌发了财,却因陈隋宝的离去而关门歇业。隆美洋行的介入,扰乱和破坏了河口草市的秩序和平静。适逢京绥铁路通车,河口草市移往包头,从此由盛转衰。
大伤元气的西碾房和荣升昌的衰落,标志着甘草时代的结束。河口,亦处在风雨飘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