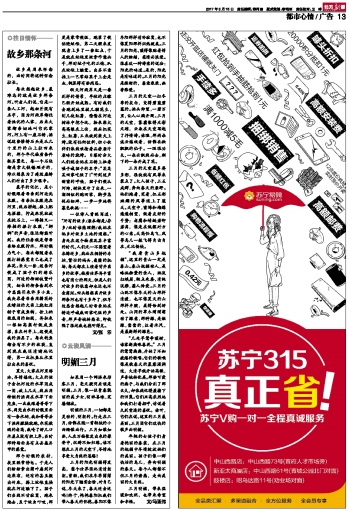| 故乡那条河 |
◎往日情怀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而时间将这种怀念拉长。
每次想起故乡,最难忘的就是故乡那条河。听老人们说,它是一条人工河,起初并没有名字,因为河两岸都住着姓沈的人家,后来大家都亲切地叫它沈家河。河上有一座石桥,据说这些修桥石头是从几十里外的山上拉回来的,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每一个石块都是拿大铁锤砸开的,难以想象为了建这座桥人们付出了多少艰辛。
最早的记忆,是小时候跟着母亲到河边洗衣服。母亲把衣服泡在河里,然后捞起,抹上肥皂搓揉,拧成麻花状放在枕石上,一棒槌又一棒槌的捶打衣服,“梆梆”的声音,很远都能听到。我的任务就是帮母亲给衣服拧水,那时候力气小,每次都随着衣服打转感觉自己也成了麻花。长大一些,这条河便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河边的柳树枝繁叶茂,细长的柳条垂到水中总能引来许多小鱼,我央求着母亲用绣花针在蜡烛的火苗上烧红用钳子弯成鱼钩,拴上衲鞋底用的细线,再扯来一根细高粱杆做成鱼漂,系在竹竿上,这便是我的渔具了。每次钓鱼都会有不少的收获,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把鱼从水里拉出来的喜悦。
夏天,大家在河里游泳,尽情嬉戏。大点的孩子会把河边的水草团成一团,放上几天,然后用特制的渔网在水草下面兜鱼,一次我跟着哥哥下水,网兜出水的时候里面有一条水蛇,我和哥哥丢下渔网撒腿就跑,水花被溅的老高,我呛了好几口水差点没有爬上岸。当时那种场面真有点丢盔弃甲的感觉。
那个时候的农村,夜里经常停电。于是人们纷纷拿出蒲叶扇到河边乘凉,还有的甚至搬出竹床,搭上蚊帐直接就在河边睡下了。孩子们当然不甘寂寞,跑来跑去,至于蚊虫叮咬,那
更是家常便饭,跑累了便钻进蚊帐,第二天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一些红点,于是就在蚊帐里捉拿作案凶手,那时蚊子吃的正饱,趴在蚊帐上睡觉。出其不意拍上一巴掌结果手上全是血,倒显得有些残忍。
秋天河两岸又是一番别样的情景,早秋的庄稼已经开始成熟。有时我们会跑到地里拔几颗花生,刨几块红薯,偷偷在河边树林中挖个坑,拾来柴火高高架在上面,然后把花生,红薯,玉米放到柴火上烤。没有任何佐料,但小伙伴们依然哄抢着品尝原汁原味的烧烤。日落时分大人们就会站在石桥上扯着嗓子喊孩子的名字:“某某某回家吃饭了!”听到这声甜蜜的呼唤,孩子们便从河滩,树林里冲了出来,一溜烟似的跑回家,脚步急促而细碎,一步一步地将暮色收拢……
一位诗人曾经写道:“所有的故乡/原本都是/异乡/此时谁能理解/我站在他乡对故乡土地的遐想。”身处在这个物质及其丰富的时代,人们无一不渴望着衣锦还乡,然而在拥挤的车站,繁忙的码头,轰隆的机场,每天都在上演着背井离乡的故事。物质世界再丰富也有消亡的那天,但是人们对故乡的依恋却永远也不会腐烂。回头想想离开故乡那条河也有十多年了,但耳边总会想起儿时母亲站在桥边呼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那声音婉转悠长,即使隔了很远我也能听得见。
文/张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