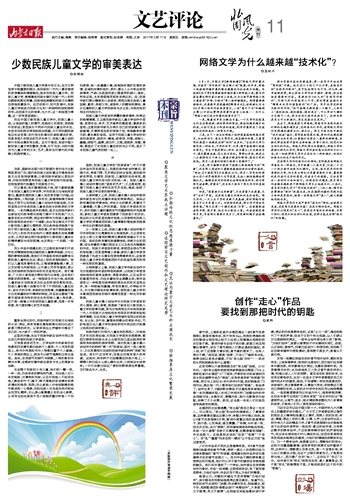|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审美表达 ◎张锦贻 |
|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中华文化、东方文明宝库中极重要的部分,各民族的一代代人最早接受的思想熏染和情感陶冶,就来自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儿童文学,寄寓着各民族长辈们对新一代人的热切期盼和殷切希冀,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精粹自然地深藏其中。在历史前行、时代发展中,民族儿童文学就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积淀和独特符号;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光大中,这一积淀更为厚重,这一符号更显美妙。
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民族儿童小说,以其曲折感人的情节、优美动心的语言,受到格外的欢迎;更因其对不同年代民族儿童生存状态、生活状况的深切审视和深刻把握,对不同时期民族地区社会变革、时代变迁的真切反映和真实折射,而具有恒久的深远的艺术生命力,民族儿童小说的单行本和合集时有出版。这对于推动、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对于充实、兴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文本、艺术,具有无可替代的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
一
当前,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中华文化影响面更加广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使各民族文化自信持续增强;少数民族作家就以更加开阔、开放的视野思考民族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自觉地使现代性灌注于民族性之中。
可以看到,他们脚踏民族大地,努力勘探独属于本民族儿童的文学世界,并向民族文化传统深层复归,重新发掘民族儿童小说自身的魅力内涵;在题材提炼、人物刻画、文本形式、美感神韵等方面体现出不同于以往民族儿童小说创作的新品格,又共同呈现出中华各民族儿童各自成长的殊异的文学景观。一系列精品佳作的涌现,显示出民族作家们在新世纪仍然将眼光和笔力集中于本民族广大儿童居住的乡村牧野,把这些村野作为民族儿童生存和民族现实进步的一个缩影,由此写出南北方不同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理特质,写出各种各样独具个性的不同少数民族儿童人物形象,并将不同民族地区中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思逼真生动地展露出来,从而反映出现代性进程中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精神遭际与实际困境,也反照出一个时期、一段历史。
而从作品中洇漫出的,又正是民族作家们不动声色却精湛独到地刻画民族儿童精神面貌、文化心理的敏锐和细腻,是他们不作渲染却俏皮幽默地勾勒民族儿童所处社会、周边人际的机智和婉约。他们以儿童视角看待生活,以稚诚情愫触摸人事,又以历史眼光判断现实,以天真心灵抒写感受;更以各自的独特的民族民间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广大的少数民族村野的现代化转型,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转型波及中华大地,各民族儿童的成长自然就涉及社会的深层变革和变动。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看似只写了不同民族儿童在生长、成长中的平常、琐细的生活故事,却蕴藏着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时代精神的特征,而且由此塑造了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活生生的民族儿童人物形象。这不是一般意义中的讲民族儿童故事,而是一次有深度、有力度的精心的艺术构建。
二
置身全球化时代,民族作家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表达,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简化和归化成大家都习惯的样式。以致常常在众声喧哗中淹没了自己的、与大家不一样的声音。
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用以发出自己声音的民族文学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都归结到个人感受、个人书写的层面上,将书中布局和书中人物都归置于个人感触、个人审美的表达上,然后予以细节饱满的立体化呈现。其间,生活细节的细巧与细腻,人物形象的丰满与丰厚,全都依仗着作家在语言方式上的革新与创新。
无论哪个民族的少年儿童,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仍各有各的脾性和气度。如壮族人对少年的昵称、对事物的另称,以及对别地人不知而当地人熟知的竹子、蜂子、鸭子等等的言说情状和表述情态的殊异、别异;如土家族人对传统歌舞的格外痴迷和一心推崇,如拉祜族人对先祖先宗开拓创业的顶礼膜拜,对山泉山溪赐惠众生的全心崇敬,从而写出拉祜族孩子自小就能郑重对待每一个汩汩泉眼、每一条潺潺小溪,就能始终维护至尊的亲情、至诚的友情的拙朴、质朴;都令人从中体会到民族情味、气韵,也极显民族心理差异的细小、微妙。所有这些,本来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民族作家们要以精湛的小说语言,表现出南北各族儿童坚毅、勤劳、孝顺父母、诚信待人的德性和脾性,展示出蓬勃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乡土性、与现实性的相互衬托和交叉。
民族儿童文学语言所表露的意味情味、所表达的格调情调,又正是民族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思维、思想状态,学术、艺术修养的最直接、最具体的显现;正是民族作家充分表示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尽情表现自我的审美个性、审美趣味的最天然、最本真的呈现。运用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各民族语言,或质朴、精准,或奇异、利落,或耐心、蕴藉,或轻巧、幽默,或古朴、文雅,或跳跃、有趣,等等,都显示了本民族儿童生活的与众不同,显示了本民族儿童气质的独一无二。
三
显然,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语言”,并不只是在作品书写的层面上,而是民族作家创作意识、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艺术表达的综合呈现,是民族作家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儿童观的生动体现,是民族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复归到“语言的艺术”,又正是拓宽、拓展了民族儿童文学所及的艺术空间,推进、拓深了民族儿童文学自身的美学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是民族作家生命记忆和童年体验的审美表达。其间必然有着民族抒情传统、诗性文化的素质,有着当下儿童情趣、天真心声的质感。民族文学语言的古朴、质朴因新儿童的蓬勃生气而重新鲜活并完美展现,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浸渍了民族悠久的历史、悠远的文化而更显优雅并恬美;从而使特定民族儿童文学的诗意美因民族儿童情愫的稚拙美而独具一种无比的清纯的美感。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既不可失却民族文化寓意和本土地域色彩,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细密地缝合于文本内里。其间自然有着民族道德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但也有着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各式先锋潮流的冲击。民族文学语言的奇诡、奇丽因全球化气势的咄咄逼人而更显得意义卓著,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渗透了先进文化意识而更觉得意味深长;这就使民族儿童文学的哲理美因时代的迅猛发展而别有一种无限的深邃美。
从特殊意义上看,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充分挖掘民族母语的特色和韵味,让民族文学语言传统独有的直觉呈象性、表里穿透性,以及运用中的高度灵活性、内在丰富性完全展露出来;使作品语言以一种极具民族神韵的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来,有一种流畅而蕴藉、夸张而真实,亦神秘亦平凡、亦文雅亦随俗的叙事效果;使民族儿童文学的本真美因民族性的格外强调而更显一种无尽的韵致美。
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对民族文学语言的用心提炼、细心探索,既更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叙事风貌,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华各民族新一代人对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现实的审美体验和美学情趣,它在民族儿童文学领域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本土性、当代性、童稚性相糅合的奇妙状态,巧妙地显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研究中深远的开拓意义和深刻的美学意义。
民族作家们对现代儿童生活的再深入、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再创造、对民族文学语言的再熔铸,都因为鲜明的民族化本土化倾向而凸显出独异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美学视野。面对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种种“第一次”和首创,面对一些人数较少、文化发展相对后进的民族作家的种种“突破”和奋进。我们不应当苛求;而是应当抱有更大的希望。这就如,树的种子已经播撒在民族大地上,一棵棵小树已经从山坡山脚长出来,小树就会长成树林;一只只幼畜已经在广袤的牧野草原生养繁殖,它们就会长大、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