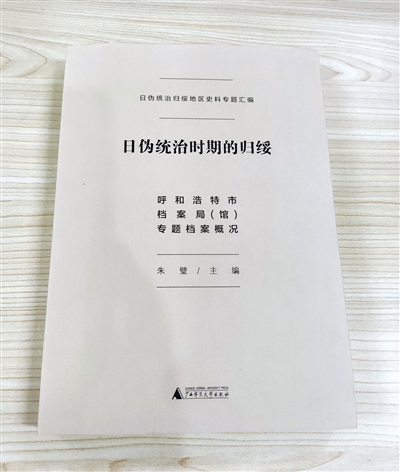车终于在下午二时出发了。这列军用火车总共十六个车卡,车卡里都是运往前线的粮食。我跟各校的慰劳代表便睡在粮食卡里。睡的地方很小,可是人数很多,我们只好有的生〔睡〕在面粉包上。打开了卡门,朝外面望着野景。北平是一个古老的城池,建筑物大部分已呈出苍旧之色,尤其是郊外的村落,那种荒凉的样子更是我们所意料不到的。到了将近抵达南口站时,我们的机车不知为什么损坏了,等了半天才由南口站来了另一部机车,把我们的军用车拖到南口站去。这当儿,天色已经黑下来了,风也刮得有点刺骨。因为列车要爬上居庸门〔关〕,须分为三段,用二部机车前后的推与拉上去,所以我们便利用这时间进南口站的市街上吃晚饭。吃完晚饭,我跟一位同行者到鞋店里去买了一双棉鞋,花了一元三角,又到帽店里去买了一顶皮帽,花了一元。回来车站里,推第一段车卡上居庸关的机车还未回来,我便独自在车站左右溜跶〔达〕着。在一部运许多马匹的列车旁边,瞧见四五个穿笨厚的羊皮大袄的关外人,我便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很和气的答我,说是:从绥远运了一百多只马,将经过北平运到南京去;马是中央宪兵司令部购的,他们运马来的一共五个人,每人的工薪是二十多块钱。我见他们是从绥远来的,不禁喜出望外,便向他们探询绥远的情形。一个未曾到过绥远的人,首先问的当然是天气了。那个刚才答过我的话的运马夫便说:“冷极了!咱们穿着皮裤、皮袄、皮靴,戴着皮帽,可是风还透得过,刺入了肉里去!”这说话使我吓了一跳。我便抢着问:“那么我穿这点点衣服,到了那边可不是要给冻死了!”那运马夫望了一望,从我的头到我的脚。“当然哪,这不算事的!”他泰然地说,我可急死了,恨我为什么不在北平购整了衣服才走。好在那家伙接着说:“在绥远城里就有点不同,城里是暖和多了!”可是他这话也安不了我的心,因为我到绥远去不单是不能长住在城里,而且是打算越过大青山,到收复了的百灵庙去。
跟运马夫的谈话还未完结,机车已经回南口站了,我们便攀上守车里。守车里比我们的粮食车暖和多了,里面有一个蛮大的煤炉,烧着熊熊的火,挨近生煤炉,还嫌热气太强猛哩!这守车里有一个守车长,留着一撇胡须,胖胖的个子,我们因为天太黑了,瞧不清居庸关的面目,便只好跟这守车长攀谈。
这天的晚上实在睡得不很舒适,人既多,位又小,并且合拢起来的被窝也敌不过冷风的侵袭,于是有些高唱着歌曲,来驱走了冷气,又有些在高谈阔论,打算解这寂寞的环境。我终于得了一个时间,一睡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早晨时分,车已到达了张家口,许多人都上街去吃豆腐酱,我不想吃什么,但也跟着上街去浏览浏览。张家口是察省南边的一个大商埠,与张北接离甚近,也与商都、多伦、沽源离得不很远,所以在军事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更重要的就是位于平绥路的中段上,如果这地方有一差二错,平绥路便只好给切断了。
车在张家口约停留一个多钟头,到八时五十分就由张家口出发了,出发时在我们的军用车上挂了三四个客车的车厢,我们便都跑到客车里去烤火。趁〔乘〕客车向西去的,一部分是到山西省的,一部分才是到绥远,这些人们大半是穿着笨厚的皮衣的北方大汉,那种强健的体格真是有点使人喜爱。入山西省境之后,沿途的农民住屋,比较的齐整一点,不过那种荒凉的景色,也还是南方的农村所未有的。下午一时零三分,车到了天镇。这也是一个在军事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的城镇。这镇上驻有六十八师李服膺的部队。它是跟阳高县、大同县等一样,都是绥远前线的运输道路,如果这三个城镇有什么危险,那末绥远全省的需给便要发生问题。所以在这一带的驻军,都跟兴和、陶林的守军一样,只有死守这些城池,虽至全军覆没,也不能退后一步。车到大同县时,已是下午的四点钟了,我们相率进大同县去吃晚饭。吃完了晚饭,我们在城郊溜跶溜跶〔达〕,那些高低不平的道路,几乎全是没踝的泥土,真合那一句“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老话。
车虽说是十一时开,但直至十二时才蠕蠕而动。我们粮食车里大部分的人都跑到守车去睡,留在粮食车里〈的〉只有我跟其他的两个人,和一个工友。我们四个人占一个大粮食车,自然睡得较舒服了,可是那位工友因为没带被毯,挨不了冻,半夜里就在中途下站跑进守车里去,这是我在第二天的上午,当军用车到了绥远城外时才晓得的。在绥远车站下车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怎样冷,天气委实是很暖和,这大概是一个反常的日子吧?
文/比 得(本文发表于上海汗血书店《汗血周刊》1937年8卷1期。作者具体信息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