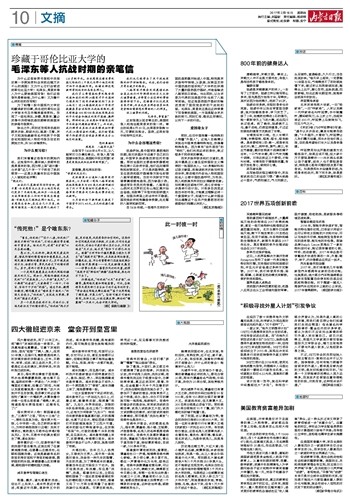| 四大徽班进京来 堂会开到皇宫里 |
四大徽班进京,用了30年工夫,把“横行”京城的昆曲一举荡平。京戏真地道也真霸道。它拿下京城的戏台,首先“征服”了满人、旗人,没用50年旗人见面行礼竟然都是纯味儿的京调京韵的京剧道白,王爷、贝勒爷、将军、巡抚、前三品的大员,不少都是红出名的票友,拜师学戏,听戏听角已成时尚。
某日,程长庚去澡堂子里泡澡,热水池蒸得朦朦胧胧,谁也看不见谁,猛然间听得一声道白:“大夫哇!”嘴里还打着板,拉着过门的弦,叫板以后紧跟着就是一段清唱:“劝大夫放开怀且自饮酒,些须事又何必这等担忧?”赢来一片喝彩声,水雾弥漫中仿佛一位苍头老者道:“唱得入味,这难道是程长庚程老板?这厢有礼了!”
程长庚何许人物?梨园著名老生,“三鼎甲”之首,“同光十三绝”之一,曾收马连良为徒。程长庚大吃一惊,心中怦然一动,自己明明未曾开口,为何仿佛刚刚张口应唱?后来才搞明白,竟然是九贝勒爷在学唱《借东风》。王爷、贝勒爷中的票友都好生了得,遑论其他?
皇帝喜好这一口,但皇帝绝不能到戏园子里去看戏,这就出现了在紫禁城建戏楼,在避暑山庄建戏台,在颐和园建戏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故宫的寿安宫和宁寿宫的畅音阁,圆明园的同乐园,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楼。
咸丰皇帝专唱青口老生
乾隆、嘉庆、道光都喜欢戏曲,但比不上后来人,咸丰热衷近乎痴迷,深爱近乎沉醉,堪称帝王中的戏迷。咸丰皇帝有戏瘾,是地道的内行,很可能是位登台就能唱戏的票友。
咸丰皇帝非常节俭,吃饭可以从简,仪仗可以从旧,甚至龙袍都可以缝补,但菊坛梨园之事不能有丝毫含糊。行头、场面、排场一点都不能差,更不能错。
咸丰戏瘾大,而且是行家。咸丰听戏开的皇家堂会只招待皇家自己人,皇后、嫔妃、贵人、常在簇拥着咸丰皇帝看戏。咸丰的堂会不容外人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保密”,咸丰戏瘾上来了,难免要清唱一段。
一位太监曾流传下来这样的话,咸丰皇帝不止一次站在九龙口上,打着云板,敲着单皮鼓,指挥着“场面”。九龙口,伶界有说法。京剧的乐队俗称场面,坐在上场门一侧的台口,这地方为何敢称“九龙口”?传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喜打鼓,打的是羯鼓,也真下过功夫,曾经因练打羯鼓打坏的鼓槌就堆放了三四大竹筐。咸丰的鼓也打得地道专业,在京剧“场面”中,打鼓的是整个乐队的指挥,足见其功夫。咸丰皇帝戏瘾上来了,还要清唱,专唱青口老生。咸丰皇帝开堂会不让外人参加,就是怕损了帝威。
夫唱妇和。当年兰儿入选秀女,又晋封为兰贵人,其中有一条就是对音乐、戏曲有一种天生的聪慧、天生的灵通,为了博得咸丰的喜爱,慈禧当年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她不但是戏迷,有戏瘾,而且是“戏精”、戏通。慈禧当权以后,立即在颐和园修了一座比故宫畅音阁还恢弘的德和园大戏楼,50大寿时,慈禧又花了11万两白银购置了全套的戏装行头和道具。可谓空前绝后,单凭这一点,足见慈禧对京戏痴迷到何种程度。
皇家的堂会也讲政治
老佛爷的堂会,大臣们都“挤着”“嚷着”“削尖脑袋”想去。
除了邀宠,大臣们、亲王郡王爷们都摸清了堂会的规律。开戏前先议政,戏中说角儿说戏,戏后议朝,老佛爷看完戏正处于极度兴奋中,办事效率奇高,真正达到耳听、眼看、手批,在金銮殿十天半个月压着的折子,戏后在颐和园须臾就办妥了。你参加不了皇家的堂会,你就享受不上这个待遇,该办、急办、非办不可的事就可能一拖再拖,拖疲拖坏。老佛爷的堂会讲的是政治,常常谈戏谈到当朝当事,谈角儿谈到亲王大臣,谈戏文谈到哪位的奏折,谈打鼓谈到谁的办事章法,那可都是“戏后吐真言”!老佛爷也是戏中人。
老佛爷开堂会,点的都是名角儿,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卢胜奎等等,名角儿的名单都是老佛爷钦点的。老佛爷尤其喜欢谭鑫培的戏,谭鑫培乃程长庚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独创谭派唱法,自成一家,100多年不变。
慈禧爱听谭老板的戏,爱谭腔,谭鑫培台口一声唱,能唱得老佛爷满心舒畅。多少烦心事,多少累不完,都在一声谭唱中化为乌有,烟消云散。老佛爷亲赐谭鑫培黄马褂,可以自由出入大内,满朝文武,满清郡王爷贝勒公侯,有哪一位有如此待遇?光绪三十三年,谭鑫培的小女儿出嫁,谁都没想到慈禧太后愣赏送一个精致的妆奁盒,这种政治待遇,细数满朝官员也少。
大洋垒起的戏台
晚清到民国初年,在北京城,有权没权,有势没势,红不红,紫不紫,入不入流,有没有派,就看你开得起开不起堂会?开什么样的堂会?能请来什么角儿?
光绪甲午年,在京城办个堂会,请动像谭鑫培这样的角儿,要花白银30两,那年代谭鑫培名气刚响,价码不高,戏份为30两白银,其他赏钱另计。
到光绪庚子年后,谭鑫培已有谭大王之称,戏份的价码已经涨至50至100两,没有150两的白银不敢请谭大王。到宣统年间,但凡请谭大王,300百两白银是必须备下的。那时候300两白银能买10个丫鬟,前门外大栅栏后的铺子能置1座。
到了民国,还以谭鑫培为例,堂会的戏份已涨到500到600大洋。民国一位财长兼银行行长请谭大王唱《武家坡》一次托出800大洋。有时候你办堂会,这些名角儿还要事先派人去看场地、看戏台、看环境、看东家,老北京话儿,先是你挑角儿,后是角儿挑你。
历史推出梅兰芳,大红大紫;杨小楼声名远赫,威震梨园;余叔岩独创流派,别具一格,此三人堂会价码俱逾千元大洋。那时期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1个月关饷350块袁大头,还不能保证兑现发洋;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管理员1个月关8块大洋的饷。如果把这3位威震京城的名角儿都请到,北京人称之为“三大件齐活”,那就要轰动京城,赏钱、饭钱、礼钱,盘点下来,没有1万大洋办不成这个堂会。(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