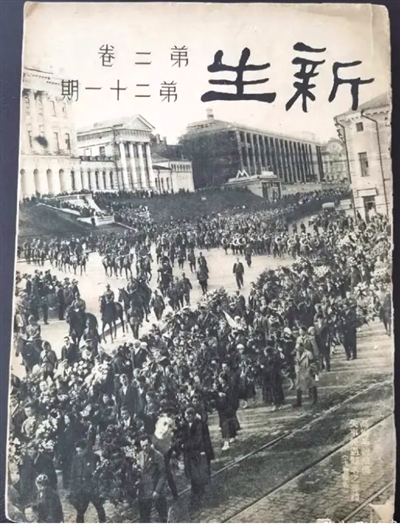久违的绥远又呈在我面前了。城还是那么方整,不再是黄土碎石道,城里城外都已铺成平整的马路。沿着路栽着平排的树木。树荫交界处立着带白手套的警察,连行人走路的方向都指挥着。铺面有的由雕栏金匾改成西式商店。女人有的剪掉了大髻。卧龙岗修成了龙泉公园。一间泥污的小茶楼新近刷了一层漆,挂起“新生活饭馆”的招牌。民众教育馆添了若干标本。日报附了新文艺创作。旧城开设了接待要人、学者的绥远饭店。这个辽远的城市似在尽其全力向现代大都市的憧憬阔步着呢。
大台〔召〕里虽仍住有百多个喇嘛,东边却辟成市场。凉粉、酸梅汤的摊子陈在魔术场的隔壁。擦了满脖子红粉的女人端坐在长条凳上,一边吃,一边听着四面交攻的锣鼓声。大台〔召〕门前就是据说曾被清圣祖的马蹄踢出泉水的玉泉井。
在建筑的美丽上,我总愿推崇舍力图台〔召〕。只它那欧亚合参的构造已够使一个对此道全然不懂的人醉心了。方的角隅嵌的是金色的装饰。梵文的字母被构成如中古月牙琴形的图案,圆圆地并立在屋的各方。雕廊的粉壁上是极富想象的佛典的壁画。殿中大柱上爬着巨大的龙身。给我们开门的喇嘛指着殿中央的太师椅,用生硬的腔调说:“这是班禅活佛的宝座。”
走到内殿,同行的友人要求他将康熙皇帝的胄甲取出来看。不很甘心的他打开了黑角落里的大箱,小心翼翼地抱出一个大黄包袱来。
他拿出一件用钢片凑成的沉重的战衣来。抚摸一下上血〔面〕的宝蓝缎,就授给了我们来端详。连那黄缎靴他都顶不舍令我们玩赏得太久。问到来历,他说:康熙帝驻跸归化时,误杀了一个蒙古亲王,惹起了蒙人公愤。
“那时候这台〔召〕都给我们的人包围了。”他立在黑的一片里,瞪大了眼说,“一个喇嘛和他换了衣服。他装作喇嘛逃走了。把胄甲留在这儿。”那人真神气,好像康熙皇帝就同他换过衣服一样。
召殿的旁廊,住有一位王爷。双髻搭在肩上的蒙古女人,用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我们。廊的柱子上贴的是些欢迎民众信仰的班禅大法师的标语。一些拖了油长辫子的喇嘛闻着鼻烟正在廊下踱步。
临行我想登城墙,看一下城中的全景,就由石砌的马道攀到北门城墙上去看。由火车上看来齐整的城是没有把握的。城楼入口处是所毛房。城楼上正摊着一大堆褴褛泥污的男孩子,扯了喉咙喊着一些由记忆中掏出的经书,而实际在用小胳臂角力玩。一个咬着红萝卜的孩子向我笑着。
看了几家仍徘徊在手工时期的毛织业。织毡工人受着最大的苦。羊毛屑堵塞着呼吸器官。一个被刀割破了手指的学徒正倚定一根柱子啼哭。毛呢在样式上虽尽力模仿舶来货,其品质之粗糙,仍毫无进步处。
在离开绥远那个早晨,我拜访了一位师长。这不是篇悼文,容我在这游踪里留下他的名字罢。刘半农和白涤州等先生动身比我早了一天。那天早晨我在绥远《朝报》上读到了“刘博士由包来绥,现寓绥远饭店”的新闻,就决定用一个熟悉的口音和面孔来惊吓他一下。
本来是同友人肃庵君偕往的,但他因怕见生人,愿在楼下等我。白衣侍者把我领到一条窄路尽头的房间。半农先生捏着他的烟卷,微笑着站在门槛处了。
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我随说话随看摆在镜台上的测音器。知道他参观了本城的学校,测过了许多处的音,并且打算日内去百灵庙。
火车时刻表不容许我多坐。而且我也没有理由用一个熟人的名义扰他学术的工作。
“有什么事我能替你在北平做呢?”
“唔”他笑了一下,把手伸到袋子里,掏出一个名片来。“请你到北平打电话给我的太太,说我在这儿平安。”
我接了片子,一面用手势往回推他,一面自己就退了出来。
被他推起短髭的微笑送出饭店的楼口后,我就匆匆地赶上了西行的火车。
五
包头是个仍带点原始朴质气的小城。包围车站〈的〉只〈是〉一片荒凉黄沙地。南边是一带黄河,闪亮地睡在南海子。城是倾斜地建在山坡上。像泥模型似的,一座座的小土屋静静地躺着。
因为是走到了蒙古地草〔草地〕的跟前,沿街走的红油脸垂着黑油辫子的人特别多,回族人也很不少。在交通上,这里几乎是个水陆的中心。平绥路的车走到了尽头,南海子长年往来着走包、宁的高帮大船。宁夏、甘州、凉州的货都以这里为尾闾。所以在商业上,便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城年轻得很。民国十二年才因为铁路的到达而设治局,十五年才成县治。但因为地势的扼要,市面上还熙攘热闹,骡轿车停在道旁,洋车夫操着山西腔,在人丛中吆喊着奔跑,繁荣中心的前街有着大门面的店铺。陈旧的富于象征性的幌子低垂在铺檐下。
东门外的转龙藏是最惹目的名胜。龙王庙建在小山阜上,瞭望着全城的土屋顶。庙后是马将军筑的炮垒山,坡上潺潺流着终年不涸的泉。这是城中住民的饮料,虽然迢迢地跑来泉水发源池处洗眼睛的也不乏人。
立在炮垒上,南可以眺望如带的黄河。坡下沙地上,不时地过着驼〔驮〕水桶的牲畜,印在沙地上静默的影子,给人以沙漠的幻象。
十五里的轿车会把一个旅行者载到了南海子。那是一片汪汪的黄河。成百只的高梆船,七站船,小筏子,各靠在河边,飘在黄水的摇篮里。船里正有人吆喊着装载货物,岸上站着些穿红襟的汉子,吹〔吸〕着烟袋,守着面前的景色。
距河岸近处是个由船户所组成的村子。他侍奉的大神是治理洪水的禹王。
“回去罢。”一位西北的长者拈着枯黄的胡须对我说:“告诉国人说,屯垦不是容易事,想速成地来发财,必至失望而归,让我们吃惯了苦的人去和自然对抗吧!如果国内有能吃苦的青年愿意和我们下田工作,我们竭诚地欢迎。响亮的口号与我们是毫无用处的。”
我翘首望那广漠的一片,我信任了生存的意志所赋予西北民众的与天人暴虐的对抗力。②文/萧 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