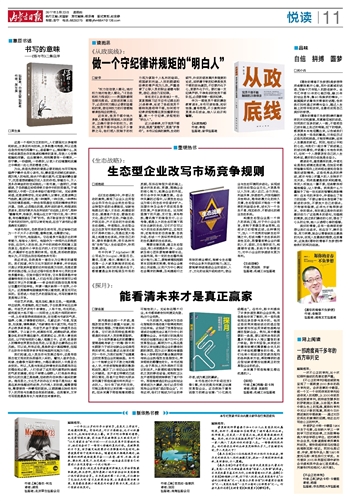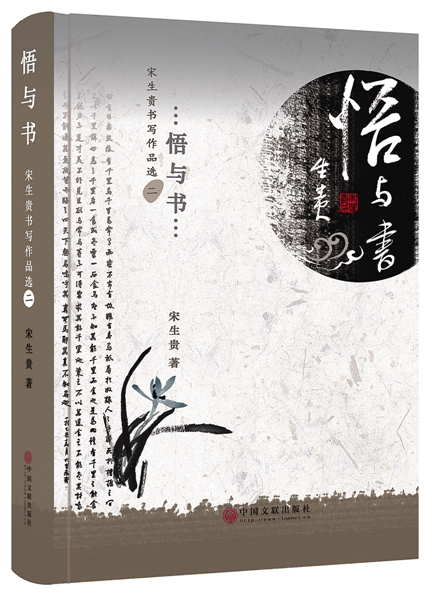| ■草原书话 书写的意味 ——《悟与书》二集自序 |
|
□宋生贵
这是一个视听为王的时代,人们要面对太多喧闹和纷扰,太多实利与时尚,太多刺激与诱惑,所以总是在急匆匆地扫视着什么,追逐着什么,捕捉着什么,其中极容易因生存的焦虑和精神的紧张,而使人心变得粗糙和浮躁。在此情境中,特别需要有一份清凉,一份宁静,一份湿润,一份柔软,以使人们在喧嚣和扰攘之中得到一处心灵的憩息之所。
为此,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必要的独处与尽可能地涵养宁静并去用心读书,如,静夜里关闭掉五彩缤纷、颇为诱人的电视,独步户外晤对星月;忙里偷闲静坐窗下,沉思遐想或翻检历史人生的存档,穿越古今,于人类永存裨益的时空间独处;一张书案,一盏明灯,开卷细读,于自然感应间领受奇文佳作中的时雨春风,于诚挚的投入中把一己生命体验付诸字里行间。无论读得闲适,还是读得悲怆,无论读得儿女情长,还是读得正气浩然,真正的读书,是一种境界,一种交流,一种养料充沛的情思滋润,一种由有限通往无限的精神世界的开垦。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所说的读书,特指读纸质读本,即如邓散木先生所说的“印在纸上的书”,那种“翻着有声,有扉页,有笔尖在文字下的行走,有一声叹息,有拍着膝盖忘了疼”的书。我不敢妄言当下是否属于读书的好时代,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当下读书的必要是确定无疑的!
与读书相关,自然即涉及到书写,而这恰恰已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值得注意,也需要讨论。
当下时代,电脑昌兴。它在诸多方面显示出的神奇魅力,每每令人惊叹。电脑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物质手段,在当代人的生活、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显而易见,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人们对它的掌握和运用,亦属顺乎社会发展的体现。但是,我却依然固执地认为,不可因此而忽视或舍弃书写!
我这样说,自然是有一番自认为立得住的道理的。我们知道,作为文化方面的许多事体,并非统统只是以求取某种直接的功利性结果为目的,而是还要讲求实践过程,以及这过程中投注身体与心灵的主体性多重体验。仅就中国汉字而言,它本身即承载并传递着特有的文化信息,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常常可以领悟到文字以外的意蕴——体会性的实践往往具有难以估量的可延伸性。所谓一滴水映照一个世界,小中见大。这是触摸电脑键盘所难以感觉到,甚至无可比拟的。至若进入书法艺术的层面而论,书写的意味则更是难以尽言。
书法艺术求美。笔走龙蛇,墨生五色,一笔波澜,呼应成势,书者陶然,视之怡然,于白纸黑字间见出神韵。书法艺术讲究个体情性。人有个性,书无同态,细究起来大抵不错——如同世上无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从形体取势到抑扬收放,往往都与书家的气质、涵养、心境、才情等密切相关。孔颖达讲:“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书家情性有千差万别,书法艺术必然多彩多姿。书法艺术益于营造一种虚灵自在的境界。于斗室之中,或展纸书写,或捧帖研读,把纷繁杂乱的世界搁在窗外,把滚滚红尘、劳劳人事丢到远处,让宁和怡悦的心融入笔墨之中。这样,容易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自由灵动,以至显示出潇洒出尘的风韵。可以说,所有这些,是虽然设计高超精密,但超不出软件中有限字体字号的电脑所无能为力的。
我们知道,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些既古老又现实的东西留存人间的。譬如人追求自由、和谐、生趣等方面的情性,大概在善良的人中是亘古未变的。所以,凡是与张扬这种情性的东西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人们住进了运用现代建筑材料造起的气派的高楼,却忘不掉青山绿野;人们有条件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驰骋,但依然向往林荫小路间的散步。推而思之,文化艺术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如此?越是在某种浪潮成热成势、灼灼诱人的时候,越需要理性,需要保持一种静观的固执,以期探趟出始终有利于人的灵性与生趣自由张扬的途路。在我看来,文字书写即是最具有长久传承的生命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