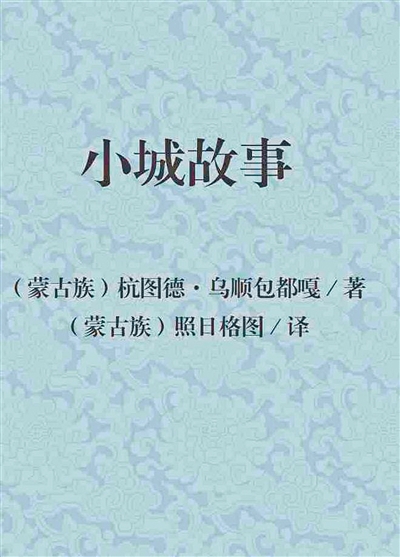一
杭图德·乌顺包都嘎,本名杭福柱,把他的笔名乌顺包都嘎翻译成中文,就是“水彩”。高中毕业后,他学过绘画,也学过医。他人不笨,只是读高中时迷上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刊,耽误了学业。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他被人挤了下去。回家务农的他,注定了不是一个好农民。后来,他去自己所在的旗县小镇,在旗文化馆谋了一份差事,编辑一本内刊,一干就是17年。
他来呼和浩特,最大的乐趣就是逛书店,每逛必买,买到自己背不动为止。他喜欢写作,写作既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刚开始写,作品没人认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奖项也常常与他无缘。他有时为此苦恼和气愤,但过后基本不往心里去,继续写他的。直到2000年,《二连》(《小城故事》的蒙古文版)出版后,他才真正受到关注。从此他笔耕不辍,写了《二连》《一生有多长》《宿命》《情敌》《飞尘》等5部长篇小说。除了写长篇,他亦写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还做文学翻译,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全体裁作家。除了诗歌中偶尔出现的浪漫情怀外,他的大部分作品常常深入现实的内里,拷问人性。
他为写作付出了很多,写作也给了他不少。2015年,他因为在写作上的成就,成了旗文化馆的一名正式员工,结束了长达17年的临时聘用生涯。那时的他,已年近50。对杭图德·乌顺包都嘎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归宿,有了生活上的保障,他便可以静下心来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尽世态炎凉,写尽人间冷暖。在国外,很多大作家都喜欢在小镇生活。而我们惯有的思维里,地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资源和人脉,我希望地域对杭图德·乌顺包都嘎的影响越来越小,真正让他的作品冲出局囿,走向更大的舞台。
二
《小城故事》,注定是一部迟到的作品。它的蒙古文版《二连》一书在国内蒙古文小说界初现,是早在20年前。那时候,杭图德·乌顺包都嘎根据自己1994年在二连浩特市工作的经验写下了这部小说。小说出版时,他刚过30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写的年纪。这本略显通俗的小说,因为它新颖的写法,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探索性描写,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是蒙古文小说里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内蒙古的文学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的情节较俗,无法称之为严肃文学,有人则认为它是蒙古文城市文学的首部长篇小说。如今,关于《二连》的种种争论已尘埃落定,而这部作品还在重印。
大概在三四年前,有一位来自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朋友,委托我从呼和浩特的书店找一本《二连》寄给他,然而我走了好几家书店依然没有找到。20年前,我读大学时,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的《二连》借阅量较多,书角被折得几乎要掉下来。我第一次阅读,亦是这部小说最火的2002年。当我看到小说中的几个家庭相继没落,为他们的命运感到悲凉时,小说结尾处孩子的啼哭声,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希望。
三
杭图德·乌顺包都嘎开始有翻译他的代表作《二连》的想法时,已过了《二连》最火的时候。或许是因为《二连》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至今为止公认的代表作,因此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越过文字的障碍读到它。
好在这部作品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2016年度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作品,给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基本保障。然而因为身边琐事,翻译工作一拖再拖,交出译稿时,已过了5年。此时,《小城故事》的蒙古文版已没有了往日的畅销效应,读者更有机会抛开其他元素的干扰,静静地去品读,去发现它的文学价值。
因为我对这部小说的叙述模式和语言风格较为熟悉,翻译工作异常顺利。翻译过程中,我亦通过作者的叙述,重回20世纪末的二连浩特,体会了一把小城里的人情冷暖。译完《小城故事》,我对它的核心内容依然放心。我在翻译过程中,甚至找到了那个躺在内蒙古大学男生宿舍的上铺、津津有味地阅读《二连》的自己,或许这就是文学的记忆吧。
如今这本书通过翻译走上了更大的平台,究竟触碰您怎样的文学记忆,还需要您的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