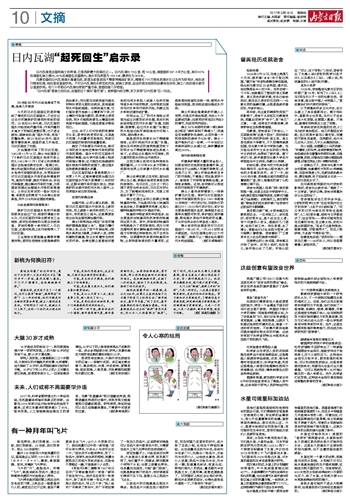| 留英经历成就老舍 |
初到伦敦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荡几十天后,舒庆春(老舍)终于抵达英国。“德万哈”号客轮停靠在蒂伯里港,码头到伦敦市区20多英里,通关后,他还得再坐半小时火车。在坎农街一下火车,他就看见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易文思告诉舒庆春,住处已给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伦敦北郊的幽静市镇,合租者是舒庆春好友,作家许地山。
两年前,在正直的满族牧师宝广林影响下,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郑重启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征引宗教故事,来表铲除社会积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结识了许地山,一见面就觉得“这是个朋友”,同时结识了担任牧师的罗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学教书,不久因精神崩溃回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为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讲师时,他想到了舒庆春。接下来近5年,舒庆春要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年薪250英镑。
初到伦敦,老舍与校方和房东都相处得和平,但许地山很快离开,使他的乡愁愈发浓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开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广场,那儿离著名的诺丁山和海德公园不远。
老舍与英国人克莱门特·埃支顿同租一楼,后者正在东方学院学中文。他和埃支顿互相辅导语言,还帮对方翻译了《金瓶梅》。初版扉页上,埃支顿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但老舍对这段经历长期缄默。
埃支顿交游广阔,令老舍窥见伦敦底层社会。一位年轻工人,谈吐很好,却时常失业,是个社会主义者。有个可爱的小老头,通晓好几门语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们讨论东西方哲学,却只能帮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与罪恶”。
在楼梯边的小房间里,老舍真正开始了创作。初写小说时,他没信心,给许地山念了几段。许地山回应:“可以,往下写吧!”3年间,老舍写出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部分《二马》。3部小说,均获著名的《小说月报》刊载。
成为小说家
1928年,老舍搬进伦敦市区的托林顿广场14号,写完了《二马》。《二马》写马氏父子一年的伦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
父子俩遇到许多文化冲击,还分头爱上了房东温都母女。朝夕相处中,温都母女也发现,马氏父子没杀人放火吃老鼠,还颇惹人喜爱。不消说,爱情终因种族主义成了悲剧。
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的生活,《二马》或许离他很近。他几次跟朋友讲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饭,而遭饭厅服务员奚落。在英期间,他只与几位华人交好,几乎从未摆脱孤独。
在小说里,他描摹过小马的孤寂:“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像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小说寄出不久,老舍与伦敦大学合约期满,他拿着校方发的80英镑路费,在欧洲周游3月,在新加坡执教半年,攒足路费,终于回到故乡北京——当时已改名北平了。
当问起那段英国时光对老舍的影响时,老舍长女舒济说:“造就了一个文学家。”舒济记得,老舍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和但丁。
老舍曾批评自己的许多作品。《老张的哲学》文字“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赵子曰》结构强了,“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二马》更丰富,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但没写完——原本可能有发生在巴黎的后传,且立意太浅,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而且人物狭窄,大多是“中等阶级”的。
他谦逊地总结:“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评我。”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