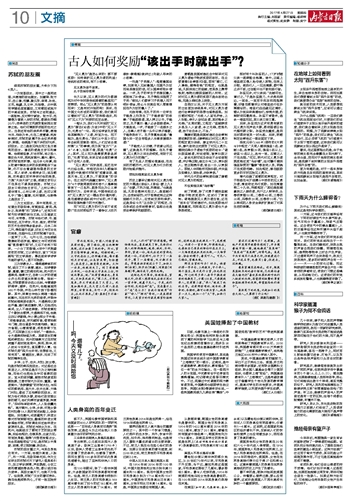| 官癖 |
学而优则仕,中国人对做官向来有好感。得了禄位,想让他挪挪屁股,还不如要了他的命。所以,官员引咎辞职者,鲜矣。明朝时候,一太守死在任上,仍阴魂不散,每日黎明点卯时刻,必乌纱束带,打扮整齐,坐在堂上,接受胥吏朝拜。太阳一出来,他就消失了。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一位乔姓太守来此上任,听说此事后,说:“此有官癖者也,身虽死,不知其死故尔。”第二天,不等死鬼来,乔太守就坐在了大堂上。死鬼如期而至,见大堂上已有人坐在那里,非常沮丧,长吁一声,悄然而去,从此不再来。(清·袁枚《子不语·官癖》)
今天,人们对“官”仍有感情。哪怕退休后,甚至被免了职,见面仍以某人的职衔相称,赵局、钱处、孙科、李所,官进一位,姓氏后边的官衔也便进一位,不这样叫,似乎少了一层近乎,薄了一层情谊,双方都不自在。毕竟老祖宗就这么干了,如杜工部(杜甫)、阮步兵(阮籍)、刘宾客(刘禹锡)等,相沿成习,想改也难。
这倒也无可厚非,怪就怪在,官场之外,仍有人觉得姓氏后面不冠以一官半职,就羞于见人。于是,我们会听到、见到各种“总”。实在靠不上个“总”怎么办?自我介绍就用“作家”“诗人”“顾问”等词,一是显得有学问,二是官方的作家是跟官阶挂钩的,这样也能自我满足一下,或唬唬人。而有个一官半职,即便退休后,也要把自己原来的职位印在名片上,一大堆原党政机关的头衔,一大堆学会、协会的帽子,着实吓人。可见人已退位,官瘾未退。
那没当官的咋办?好办。倘若识得一字半句、三两数目,中个举人,捐个监生,虽不是什么官,但也很过瘾。阿Q的同乡举人老爷干脆连前面的姓都免了,方圆100里,只要提起举人,没有第二家,“举人”就成了他的名字。还有那卖唱的、说书的、算命的、杀猪的,都可以称为官人,钱再多一点儿,就加一个“大”字,如西门大官人。
若还不过瘾咋办?也有辙。房地产开发商早就替你想到了,开车围着城市绕一圈,遍地都是“某某邸”“某某府”“某某阙”,何等气派。虽是平头百姓买个庇身之所,但就爱这个名,冲这名字,也要买1套,住进去,过把瘾。
看来官瘾实在难戒。近日,报载某监狱长向记者介绍说,已失禄位者在大墙内仍“喜欢其他罪犯称呼他们入狱前的头衔,渴望得到狱警的尊重和监狱领导的关照,希望能给他们面子”。
袁枚笔下的死鬼,比起如今的某些大活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据《 讽刺与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