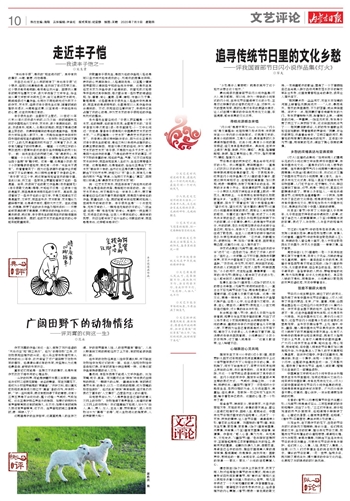作家刘霄的作品《狗这一生》,保持了刘氏话语的“天马行空”和“特立独行”。他为“低等动物”立传,对动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致。他从乌兰察布张维村走入城市的近20年中,依然保留了对广阔田野下动物书写的癖好。他津津乐道这样的书写,并坚持认为这是他最自由、舒服的书写状态。
童年记忆可能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怀,也是所有作家孜孜不倦书写的心理坐标。
一头驴的叫声,可能是惊醒村光棍二狗美梦、阻断他与邻村二姑娘见面唯一途径的噪音。可在刘霄笔下,却成为乡村世界销魂的“男高音”。“然驴之叫,却以高亢悠扬和极具穿透力而位于‘高音’者的行列,并独树一帜。”“驴一旦叫起来,便没有即刻停下来的意思,没有个三声五声是不会收场的,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气势如虹。这也正是驴鸣名声在外的原因。如果它的鸣叫光有声音嘹亮而没有时间持久,也不行;如果光有时间持久而没有声音嘹亮,还不行。当声音和时间二者兼具时,便一鸣惊人了。”
这哪里是驴的生存哲学,这简直就是人的生存之道。驴的世界里有人性,人的世界里有“兽性”。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跨越经历了上万年,有时可能很快回到从前。
他书写的动物经常在人性中获得比照,并不断在动物性中发现它们的另一面。他在人性和动物性中自由地切换,你有时很难分辨出是哪一种。这是这部作品保持奇葩的迷人之处。
鲁迅说,有些东西是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比如苍蝇、蚊子、跳蚤。可刘霄对这类“种族”并未表达出特别的歧视,“一颗硕大的头颅,一副通体发黑(有时候还是荧光绿)的身子,以及一双透明的翅膀,成为苍蝇的标志性装扮”。他对此类“种族”虽有诟病,但对其仍然表达了基本的“人文情怀”,凸显自然主义的价值观。
马克思韦伯认为,“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动物难道不是悬挂在人类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吗?我们居高临下地把人划分为“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主流人群、弱势群体”,把人与动物划分为“高等”“低等”,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讲,人的贡献更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