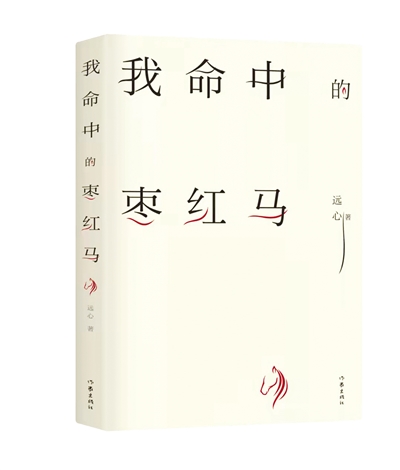诗为心声。人类不能没有诗歌,根本的在于心灵需要守护、精神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深入到最不可言表之处。优秀的诗歌和诗人,如同老练的建筑师,用语词架构出独特的宫殿,展示着人类精神的深层结构。远心的诗集新作《我命中的枣红马》,就是这样一座独特的精神之宫。
远心出生于河北,幼时迁居内蒙古,从此结缘草原、钟情于马,如她在书的“后记”中所言,她有一颗“蒙古马的心”。这本诗集的大部分作品,都与马有关。用她的话来说,马从山丘、河流、草原,从博物馆的雕塑,从摄影师的图片,从长调民歌,从中外史诗,从古典诗词,从不同方向嗒嗒走来。“清脆的马蹄声,成为诗的节奏。水晶一样的灵魂,照进诗的灵魂”。于远心而言,马是美丽的生物,也如奇幻的精灵,已成为她精神的化身,寄托着生命追寻。“肯德基的玻璃窗外/来往都是都市的汽车和行人/我定睛细看,再看/依然看见草原:漫坡,向上,几道山棱”“有人坐到窗前/我还是看到她背后的草原”(《窗上》)。可见,这种精神已融入了诗人的主体意识,一触即发,自然流淌,挥之不去,去而复返。
当远心以诗的语言诉说她“蒙古马的心”时,在抽象化重塑中完成了意象的超越和营构。而这个弥漫在整本诗集中的意象,超越了“马”的具体视觉内涵,转化为“奔跑”。也正是“奔跑”,给了远心的诗一种流动感,使之成为身体阅读的对象。或因这个缘故,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虽稳坐在家中的沙发上,却产生了移动的体感。
被远心收入笔下的那些“马”,几乎都是奔马,请看:“你奋蹄疾驰,让尘土飞成光轮”“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我命中的枣红马》)、“黑马甩着一身的阳光甩得再快一点”(《啸鸣》)、“一群野马奔驰在连绵不绝的山林间/忽而踏入深谷/忽然腾跃峰岭”(《野马鬃鬃》)、“风中奔跑的小黑马/像顽皮的小驼羔,小狼崽,小骆驼/黑黝黝地拱我的额头”(《科尔沁小黑马》)。而在《厩中》这首诗中,远心更开宗明义地吟到:“这几乎没有可能/让一匹野马入厩,厩中”。在她的心中或笔下,马是永动的性灵。
当然,奔跑的不一定是马,可能是山羊:“什么时候从羊群里跑出来/脱离西鄂尔多斯大地/穿越荒漠、平原/到阴山”(《一只阿尔巴斯山羊》)。也可能是风:“奔腾起来,呼啸而至/摘下小马驹的桂冠/风翻起帽檐”(《巴尔虎女人》)。或是火车:“列车,穿越大兴安岭/乌奴尔,免渡河,博客图,兴安岭/从西麓钻进去”(《穿越大兴安岭》。抑或地铁,“一条潜伏的铁皮蛇/突然蹿出,绿眼睛,盯着我/弯曲,转向,尾巴摇摆/呼啸而去(《空心蛇》)”。还有不舍昼夜的时光或曰思念,“当你再回来/深深的思念已贮满心怀”“当你再回来/长长的等待已随花开/照片已摆在蒙古包里/我已消散在无影无形的风里”(《带不走的花斑马》)。
“马”浓缩了远心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成为诗人内在世界的修辞。“奔跑”则比“马”更具本质感,从而完成了“马”的精神抽象与移情,一如鲁迅笔下滋长得有些野蛮的“野草”,也似昌耀诗里的静穆而显出神性的“高车”。诗心一片枣红马啊。世界因此而兴奋地跃动起来,焕发出内在的节奏。而节奏,恰是新诗的本质规定所在。
自新诗诞生以来,诗人和诗评家们为押韵问题聚讼不已。押韵在本质上应是文字的音乐感或曰节奏。我记得谢冕先生说过,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否则,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表现这种音乐性的重要途径在于内在的节奏感。赋予或激活诗歌的节奏的办法当然有许多。在我看来,远心这本诗集,似乎打开了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扇窗。
在她的诗作中,语言技巧有时成为节奏感的来源。比如《啸鸣》:“窗外的鸟叫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早晨来得再早一点/光在窗框上打得再白一点/再白一点白到发金/爱退却之后距离再远一点/再远一点不产生嫌恶不要仇恨自己”。但更多时候,还是通过意象及其营造过程,带出那种属于诗的节奏,或拙重或奇巧或轻灵或缓滞,激发着读者内心的音乐感。
早在80年代中期,昌耀曾经表示,他欣赏从生活感受中升华的、渗透了创作者主体精神的艺术真实,“心境辐射的真实,形变实即情变的真实,梦幻的、乐感的、诗的真实”。我以为,《我命中的枣红马》这部诗集,贴切地展现了昌耀所欣赏和守望的那种艺术境界。在书的“后记”里,远心把自己比作一把马头琴,“被草原上的老牧人拉出苍凉的长调”,那么,让我们静心聆听这来自高原的宽广旋律吧,在诗句里,在书页间。
(作者系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