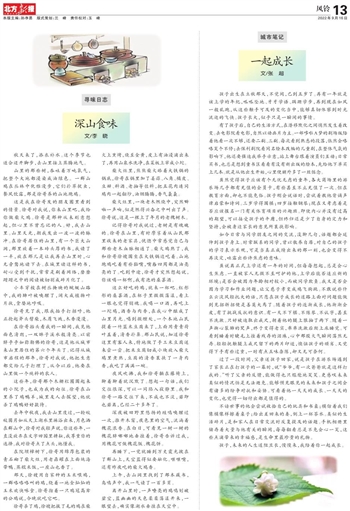秋天来了,添衣补水。这个季节也适合迈开脚步,去山里接上蒸腾地气。
山里的那些树,吞吐着万吨氧气,把整个大地都浸染成油绿色。 一群山鸡在丛林中优雅漫步,它们扑草捉虫,餐风饮露,那是徐哥养的山地跑鸡。
这是我在徐哥发的朋友圈里看到的情景。徐哥对我说,你来山里吧,我给你做柴火鸡。徐哥是那种从未刻意想起,但心里不曾忘记的人。好,我去山里。山里天光,朝我发出一波一波的脉冲。在徐哥居住的山里,有一个巨大山洞,那里放着一本砖头厚的书,我读了一半,放在那儿是让我再去山里时,心无旁骛地读下去。在城里读这样的书,耐心受到干扰,常常是刷着网络,磨磨蹭蹭之中的阅读被切割成碎片化了。
小车穿梭在树丛掩映的蜿蜒山路中,我的肺叶被唤醒了,阔大成植物叶片状,贪婪地呼吸。
徐哥见了我,跟我抬手打招呼,他正抡起斧头劈柴,木屑飞溅,木香漫漫。
在徐哥抬头看我的一瞬间,我见他面色清朗,一双眸子溪水般清亮。以前胖乎乎如弥勒佛的徐哥,这是他从城市来山里居住的第六个年头了。记得从城市启程的那年,徐哥对我说,他把生意都交给儿子打理了,从今以后,他要在山里做一个纯粹的农人。
这些年,徐哥那个木栅栏圈围起来的小院子,也成为我的向往。徐哥在山里养了鸡鸭羊,城里友人去探望,他就杀了鸡鸭好好款待。
去年中秋夜,我去山里度过,一轮皎皎圆月如从天上湖水里淋浴出来,月色洒在群山中,徐哥对我轻声说,你这些年,一直没放弃在文字田园里耕耘,我尊重你的选择。我对徐哥点了点头,他懂我。
在院坝樟树下,徐哥用绵厚包浆的青石砌了柴火灶,用老鼎罐在上面炖海带鸭、蒸糯米饭,一座山也香了。
那天,徐嫂用自家种的玉米喂鸡,一群咯咯咯叫的鸡,绕着一地金灿灿的玉米欢快啄食。徐哥指着一只鸡冠高耸的公鸡说,今晚就吃它吧。
徐哥杀了鸡,徐嫂把拔了毛的鸡在柴火上熏烤,烧至金黄,皮上有油浸滴出来了,再用山泉水洗净,在菜板上宰成小坨。
柴火灶里,熊熊柴火舔着大铁锅的锅底,徐哥在锅里加了姜蒜、八角、橘皮、豆瓣、料酒、老抽等佐料,把五花肉连同鸡肉一起翻炒,油烟腾腾,香气袅袅。
柴火灶里,一块老木燃烧中,突然噼啪一声响,似是燃得兴奋之中叫出了声。徐哥说,这是一棵上了年月的老槐树木。
记得徐哥对我说过,老树是有魂魄的。徐哥在山里,有时摩挲着从山民那里收来的老家具,恍惚中常感觉自己与那些老木血脉相通了。柴火鸡熟了,我和徐哥徐嫂围坐在大铁锅边吃着。山地跑鸡吃着有些黏嘴,嘴唇四周都是油亮亮的了。吃到中途,徐哥才突然想起说,你该喝一杯啊,我有泡的桑葚酒。
这么好吃的鸡,就来一杯吧。红彤彤的桑葚酒,在杯子里微微荡漾,看上一眼也觉得销魂。我喝一口酒,再吃上一坨鸡,酒香与肉香,在我心中酿成了山里月光。喝到微醺处,一个本地山民提着一竹篮米豆腐来了,上面用青青荷叶盖着,清香扑鼻。那山民说,知道徐哥这里有客人来,特地做了手工米豆腐送来尝一尝。把米豆腐切成小块放入柴火鸡里煮熟,豆腐的清香裹挟了一身肉香,我吃了满满一碗。
夜风吹拂,我和徐哥躺在藤椅上,聊着聊着就沉默了。想起一句话,我们交往很深,可以一同陷入寂静里。我和徐哥一路交往下来,不咸也不淡,若即也若离,已经二十多年了。
深夜被田野里悠扬的蛙鸣唤醒过一次,推开木窗,夜色里的空气,流淌着槐花浓香。在白日,可看见一树一树的槐花胖嘟嘟地垂挂着,徐哥告诉过我,用槐花可做槐花饭、槐花饼。
再睡下,一觉就睡到万丈霞光披在了群山上,天空蓝得似要融化。咂咂嘴,还有昨夜吃的柴火鸡香。
上午,去山洞里找到了那本藏书,鸟鸣声中,我一气读了一百多页。
离开山里时,一声嘹亮的鸡鸣划破碧空,蓝幽幽的天色柔柔荡漾开来,一眼望去,确实像湖水垂挂在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