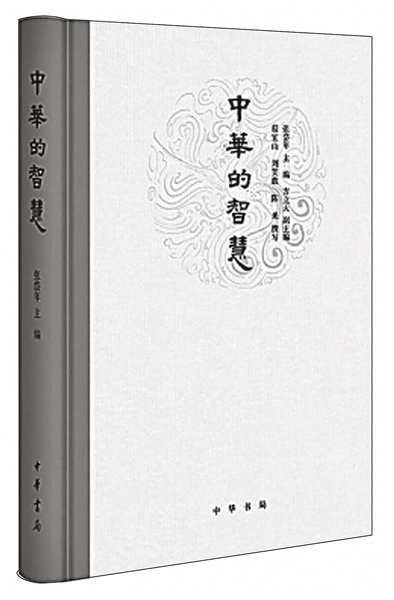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比较全面、科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包括中华思想的意蕴理路、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以及诸种通向致知明理的方法论。
“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对“道”的理解可谓简洁明快,切中要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哲学家的新高度。他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
作者对每个哲学家的把握都是斟酌再三,力求概括大略,窥其奥秘。比如论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过犹不及”“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为题;论王弼以“得意忘言”“本末与体用”“名教与自然”为点;论张载则以“虚空为气”“凡象皆气”“神天德,化天道”“一故神,两故化”为焦点。凡此种种,都能以问题为切入口,提纲挈领,擘肌分理,原原本本,直逼本相,体现了醇正平实的学风与独到的哲学史识见。职是之故,作者探赜辨析的哲学史难题就能水到渠成地展现出来。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关于程颢与程颐,书中申明其共同性:“他们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境界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作者论程颢以“浑然与物同体”“动静皆定”“天人一理”等为题,论程颐则以“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动为天地心”“道则自然生万物”等为题,精准地反映出程颢以发明本心为取向、程颐以居敬穷理为职志,分别开启不同理学路径的哲学史事实。可谓二程各表,同异自现——这是非同寻常的出色的哲学史叙述。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作者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
这种努力是明显且有效的。比如,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和哲学史料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得出诸多新见。张岱年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建构了中华智慧的谱系,以“道”、理性精神来统摄,将中华智慧的体认纳入严肃的学理观照与高远的历史观照中,并将对中国特色人文精神的孜孜以求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