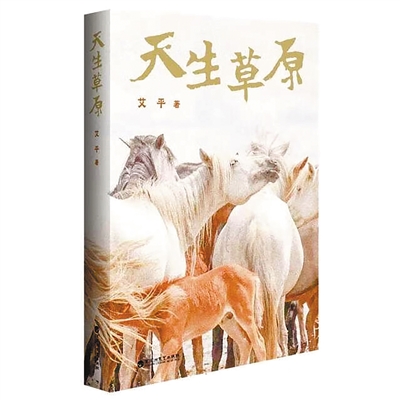艾平是生活在内蒙古大地上的著名散文家,从早期的散文集《长调》《呼伦贝尔之殇》《雪夜如期》《风景的深度》《草原生灵笔记》《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平用整整四十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
我们走进呼伦贝尔草原,实则已踏入一片精神原乡——那里不仅是地理版图上的绿色疆域,更是文学的一片星空。艾平勤勤恳恳地在这里劳作,构筑起一座独属于她的文学圣殿。《天生草原》作为最新力作,绝非27篇文字的简单缀合,而是一位草原女儿与天地万物对话的完整史诗。这部作品既延续了她对草原生态、游牧文明及生命哲学的深度勘探,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在自然与人文之间,发掘出了潜藏的神性光芒,从而牵引着读者的情感波涛和精神向度。
《天生草原》中有天地精神与草原魂魄。艾平的散文境界,既辽远广袤又温暖可亲。文字间流淌着牧歌的韵律,深邃处见平实,平实处蕴力道。她以忠实记录者的姿态,将草原的日常琐碎升华为现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注脚,让每一株草叶都成为文明的密码,每一阵风都化作历史的低语。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天地精神相融合的书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地域文学的局限,成为当代散文创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艾平作品生动展现了她如何将生命融入这片浩大草原,如何以深沉的爱拥抱这片多情的土地。无数个零下三十度的冬日,她为观察驯鹿、犴、猞猁等生物的冬栖习性,连续在深雪中跋涉,肢体几近冻僵,仍坚持记录每一处细节;无数个炎夏,她席地盘腿坐在牧民的蒙古包外,一边聆听老额吉唱着古老歌谣,一边在笔记本上飞速记录即将消逝的声响;或深入人迹罕至的森林,追踪着鸟儿幼崽的成长与一天一变的植物,浑然忘我。这种用身体感知大地的写作方式,让她的文字带着青草的气息与风雪的体温,也使她成为草原最忠实的记录者与最深沉的热爱者。在《驯鹿之语》中,那些朴素的写实与科普背后,是她反复求证、多方查访的严谨。她也曾为确认一个关于蒙古马的历史细节,数次造访一位老牧人,核对不同季节马匹的生理变化与行为模式。她不仅采访牧民,还请教兽医、生态学家,还多次跟踪各种马在山野里的行走。扎根大地,融入生活,也使她的散文兼具诗性美感与文献价值,既可作文学文本欣赏,亦可为研究草原生态与游牧文化提供参考。
《天生草原》中见生态伦理与文明对话。艾平的自然观察,自然地延伸至文化习俗与历史传承层面。这种文化深度亦见于《锯羊角的额吉》《萨丽娃姐姐的春天》《羊群中的一只雁》等篇目。对细节的执着,让她的散文充满历史的厚重感与生命的温度,让她的作品在文学性与真实性间找到了完美平衡。
艾平散文的深邃处,在于她彻底跳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窠臼,一笔一笔地构建“万物有灵”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雪无止境》中,雪是春的滋润,也是人类依赖的生存环境;《会飞的樟子松》里,带翅膀的种子如生命使者飞遍北半球,构筑起一道道防风防沙抗旱的生态长城;《撒欢牧场的白头翁》中,一种小小的野花绽放在林地上,其实潜伏着背后惊人的奥秘;《原生草》描绘碱草的坚韧,更是道出了草原的生态秩序——人需要羊,羊离不开草,草离不开好生态……《大鸟盛放如花》里,通过作者和大鸨鸟的几次相遇,写出了动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也呈现了游牧文化的生态观;《芦苇之舞》中,芦苇摇曳的意象,不仅是自然乐章的唯美,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天地与我并生”的意义;《野韭菜花是羊肉的魂儿》通过一味美食,写出了贴近自然的游牧文化记忆;《白雪森林》中,通过多种动物脚印和巢穴的叠加场景,加之对不冻河和驼鹿的讲述,写出了大森林生物链的繁复和隽永;《聆听草原》中有关于过往的生动回忆,又有今日之变带来的惊喜……艾平笔下,草原并不是美图般的风景,而是一个充满灵性、能回应、能言说的生命体。作者的这种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源于草原古老传统价值与生态意识的深度融合,以及对科技时代草原前景的思考。
在《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中,艾平以极具张力的笔触,书写了祖母与狼的共生场景。母狼微弱的呼号,在祖母的共鸣中被放大,构成了跨越物种的互助与信任。月光下,人与狼的影子交叠,构成一幅超越二元对立的生命图景。母狼为守护幼崽冒险滞留,祖母则以草原母亲的胸怀伸出援手。这一幕,不仅是生存的互助,更是草原伦理的具象化——天地万物,共享恩泽,互为依存,方能生生不息。“我亲爱的老祖母,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她笔下的牧民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生命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正如文中所言,天地给予了你和我相同的恩泽,让我们绵延子嗣,永续繁荣。我们只有互相支撑,互相给予,才能找到生物圈共生共荣的法则。在《聆听草原》中,她写道:牧民们常常说“看吧,这是我们的草原”。这里的“我们”不仅包括人,还包括马、羊、草、河流和天空。在《驯鹿之语》中,艾平诠释了这一生态哲学:生物圈之母以无数双手缔造时光之网,每一生命各有千秋,却互为依托,构成一个巨大的有机世界。这种生态伦理在当代生态书写中具有先锋意义,它提醒我们,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绝不可以像上帝那样颐指气使,主宰一切。
艾平对万物灵性的感知与描摹,构成了她散文的精神内核。在《雪无止境》中,她的雪“是我的背景,也是我的远方。雪给予我的记忆,记忆栩栩如生;我与雪的对话,没有止境。”这种处理,让读者不仅能“听见”风雪,更能“看见”它的情绪与姿态,使自然景观升华为具有情感深度与艺术张力的文学意象,更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天生草原》中的情感档案与生命坚守。作为女性作家,艾平擅长发现细节中的人生与时代。在《阿哈的金牌》中,一块普通的摔跤奖牌,串联起几代牧人与知青的命运轨迹。在文字中找回了岁月深处超血缘的深沉情感,使那些被宏大历史遮蔽的个体经验和生活样貌重新焕发光彩。
《天生草原》中凝聚着文明的韧性与天地和谐。《在呼伦贝尔的雪中》描绘的传统转场场景,《聆听草原》中记录的是即将失传的生态规则与草场的命运。《风景的深度》结尾写道:“呼伦贝尔草原的美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悠久的文明是其中最有深度的风景。”在《芦苇之舞》中,她将芦苇的摇曳与牧民之舞、马群之舞相联系,将自然与文明并置。可以说,艾平的散文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地方性知识的思考路径。
艾平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尤为难得的是,她成功避免了地域书写中常见的异域情调猎奇,也超越了风情化的浅表描绘。她的每一处风景描写都与人物的心灵轨迹严密对应。她写雪,雪落下的声音,就是天地间最轻的呼吸;写草长,绿色就会从地心涌出,漫过马蹄;写黄昏,夕阳会把影子拉长得像一首长调。这种举重若轻的文字功力,来自她对汉语音律的敏感把握,更来自她与草原气息的长期融合。在《我在大森林里找你》中,她将寻找“长生天”的过程与寻找自我内心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你是谁,却见你活生生的扑面而来,与我窃窃私语,与我促膝长谈,与我命运与共。”“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你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些来自心灵的肺腑之言,使她的散文具有音乐复调般的立体感。
艾平的散文境界辽远而广阔,在《在那百花盛开的草原》的结尾,她写道:“蒙古袍的蓝色代表天空,黑色代表大地,红色代表火。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是这样把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带在身上,放在心中,赶着牛羊,唱着牧歌,穿过霜天雪雨,穿过历史,走进了崭新的生活。这一切都发生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这种平实而富有哲理的语句,让她的散文在读者心中留下长久的回响。
读者一旦走进《天生草原》,已置身一场横跨时空的文明轶卷。《天生草原》是艾平献给草原的赤子之心,亦是草原馈赠世界的文明信物。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得以窥见草原众生的呼吸,触摸万物灵性的脉动,体悟“天人合一”的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