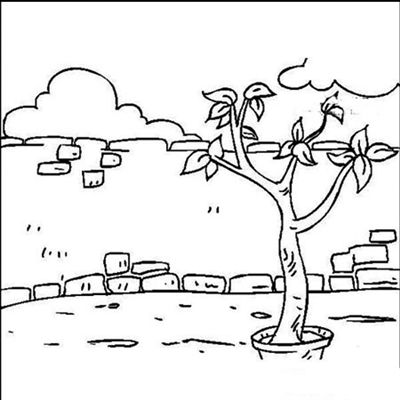沿旧医院坡而下,北边城墙与南边土梁遥遥相望,野生的枸杞树从半崖枝出,七月过后,红红的果实也实实诱人,踮着脚也够不上,便与小伙伴叠了身子,颤巍巍托着土崖站起,肩上伙伴勉强够着一、二粒,便支撑不住,一同滚倒在地上,却不忘在汗津津手掌中展出这诱人的红溜溜。
月色落满黑河中,细小的荷叶下伸出一朵朵黄色的小花,蛙鸣便一声接一声的撞着堤边的沙枣树,清香便散开来,落满城。
综合商场后面的灯光场篮球赛散场后,附近村庄的人们趁着月色,三三两两沿堤坝向家走
去,妙龄女子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大胆的必是拉了手,月光便明媚着,二、三声的水鸟声也隐去,清风荡涤着胸怀,月下故土便平添了几许相思。
梁畔沟壑中清亮的泉水如笋般冒出。晨曦中左手拿一小桶,右肩担一对大桶,不必问这便是去梁底泉子沟担水的勤谨人了。女人燃了炊烟,一瓢泉水便甜了人间,一天的光景就开始了。
南头果花嫁了丑男,邻居婶子笑话果花夫丑,果花便把油亮的大辫子甩在身后,亮亮堂堂甩出一句:我家的人丑,可我家的水瓮里从来都是满满的泉水。邻居婶婶便哑了口,她家的瓮里总是懒爷们儿从院里汲取的咸水。
民众头龙窑上的火熄了,方方正正的砖便一排排挨梁码着。吹鼓匠的金来背着手,袖筒边必是他心爱的唢呐;缓慢的身影走过陈家院门,绕过一排排新砖,折向梁,太阳与唢呐声便一同从南梁升起。
雨水饱满,南滩的水凹处便集成塘,午后总有顽皮的孩子光了身子,顾不上趿拉鞋,赤脚跑向水塘,顶着烈日,狗刨式把南滩中的老故事划开,旧日落在历史中的情景便如涟漪一般荡去,人间添了些许美好。
长大后,总想安安静静与长河对坐,相看两不厌。河水孕育万物之时,也参与对我人之初的刻画与塑造,以至于性格与神情必是光明磊落,淡泊从容。
问及母亲,曰:出生于托县黑河边衙门口大院,胎盘落于黑河边。文/贾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