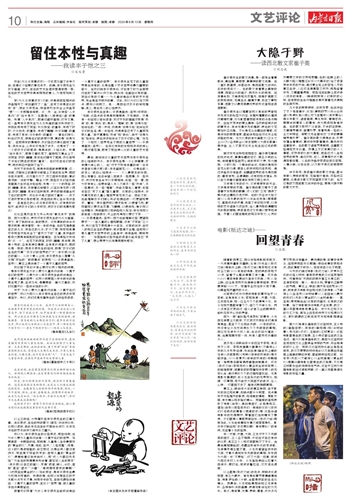我在《为儿女写真述怀》一文收尾处画了句号之后,觉得这个话题仍意犹未尽。的确,丰子恺先生为孩子画画、作文,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显得非同一般,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大有可玩味之处。
写《为儿女写真述怀》之前,我是把那些相关的作品摊开了(或曰翻开了)“品”,在写之中是在比较中“评”,而此文写完后,则继而引发我合上作品来“想”——亦即掩卷细思。这一开一合,似有些“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王国维《人间词话》语)的意味。所谓“入乎其内”,即通过翻开画册、打开文集,逐一品赏丰子恺先生为儿女所画的画与所作的文,并因此而走进了阿宝(长女陈宝)的童年,走进了软软(次女林先)的童年,走进了瞻瞻(长子华瞻)的童年,走进了恩狗(幼子新枚)的童年……看他们游戏,听他们欢笑,惊异他们的奇思妙想,真的是“设身处地”。在那特定的情境中,我们自己仿佛也回到了童年,洗去浮尘,心中似乎纯洁了许多。这是受了一个一个的孩子们的感染,是具体的,个性化的。所谓“出乎其外”,即是文章收尾了,画册和文集合上了,与阿宝、软软、瞻瞻、恩狗他们隔开了距离,我也告别了与他们同在的那段“童年”。他们还在他们的世界,而我则已然回到了当下。
我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走到窗前伸腰展臂,仅一刻间,对面林立的高楼与街面上不绝的车流声,同时夺目与袭耳。这反差太大了,我又回到书案前,意欲接续前一刻的宁静。静坐少顷,那些孩子们在我脑海里再次生动活泼地出现,先是一个一个的阿宝、软软、瞻瞻、恩狗,紧接着逐渐增多,以至似有无数个阿宝、软软、瞻瞻、恩狗们活跃起来,使我的脑海里全成了他们的世界!我也似乎再次回到了童年——我不仅很欣慰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因此而心生乐观与自信——自信自己的心还没有彻底老化,还有柔软的地方,能被孩子们的小手叩动,被孩子们的纯真所感化!
这也正是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意犹未尽”的原因。因为这感化,使我对丰子恺先生的为儿女画画、作文,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想法。这所谓新的体会与想法就是:单独看那一件一件的作品,他的笔端是画自己的儿女,写自己的儿女;扩大了想,则可知其情怀中则自然地包含了“普天之下的”儿童,其作品的感染力便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他笔下的阿宝、软软、瞻瞻、恩狗等,既是个别的,各有其神态情趣,各有其状貌言行,同时也是一般的,用丰子恺先生的话说,就是“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丰子恺《谈自己的画》)。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子恺先生从描摹“儿女相”开始的“‘舐犊情深’的表现”(《<子恺漫画选>自序》),事实上是创造了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
我们接下来似乎有必要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丰子恺先生为什么要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二是为什么丰子恺先生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这两个问题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往宽了展,往深处究,是需要做一篇大文章的,我们这里只谈一些体会性的认识。
关于“为什么要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以为可以从丰子恺先生自己的表述中获得启示。所以,我们还是先摘录他的几段话来读读: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
(摘自散文《儿女》)
我作漫画由被动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
(摘自《漫画创作二十年》)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册子里。
(摘自《给我的孩子们》)
以上三段话,分别摘抄自丰子恺先生的三篇文章。类似表述,在他的别的散文(随笔)与创作谈中,也可以读到,由此足见他在此方面体会深切,也足见与他的艺术创作之间关系之重大。
我以为,丰子恺先生的这些表述,即在说明,他为什么要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如果再做一点概括的话,那就是:儿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天真,纯粹,自然,“人格完整”;可是,这个时代是很短暂的,倏忽而过,这是任何人都没有例外,而且是不可能改变的;告别儿童的“黄金时代”,便意味着逐渐走向成人,而“成人大都已失本性”“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丰子恺《谈自己的画》),变得“退缩,顺从,妥协,屈服”甚至“虚伪”“冷酷”,“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送阿宝出黄金时代》)如此而往,是丰子恺先生最为叹惋与可惜的。所幸的是,他可以发挥自己的艺术感兴与艺术才情,利用手中的笔,自由无碍地创造出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把儿童的本性与真趣留住。
接着我们来看“为什么丰子恺先生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丰子恺先生笔下的儿童世界是他独有的,也是他整个艺术世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我们向丰子恺走近,对他有了较为全面而内在的了解与认识之后,就会说:他画出这样的画,写出这样的文章——为儿童创造出这样的艺术世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对此,我以为仅以如下两点,便足以说明之。其一,是因他对孩子的爱和理解;其二,是他本人的心性使然。
丰子恺先生在其《<子恺漫画选>自序》中写到:“无疑,这些点的本身是琐屑卑微,不足道的。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的。”“进一步说,我常常‘设身处地’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常常自己变了儿童而观察儿童。”由于真情地“热爱”和“亲近”,由于“设身处地”地体验,使他深深地体会了孩子们的心理,“发见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子恺漫画选>自序》)。他将这独到的发现和深深的爱心一同付诸笔端,即有了那出神入化的儿童的艺术世界。
最后,再说说这儿童的艺术世界与丰子恺先生的心性间的关系。丰子恺先生是一个心存善意,怀有博大爱心的人。他“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读<缘缘堂随笔>》)。这是他做人的本心,或曰心性特点——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因心有善念,他总希望人世间多一些同情,多一些关怀,并对所有生命予以平等相待,包括一虫一草;因为怀有爱心,他更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热爱”,多一些真诚,多一些“理解”,并能多替他人着想,包括将自己“变了儿童”替儿童想。这样的心性特点,与天真无邪的儿童心理世界有无缘之合。因此之故,他能理解孩子们随心所欲地提出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譬如:“房子屋顶可以要求拆走,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要求生花草,飞蝴蝶,以便游玩;凳子可以给穿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要它下来……”(《<子恺漫画选>自序》)因为他能理解这些“愿望和要求”——在儿童的心里和眼里,没有“不可能”三个字,所以在笔下表现得十分自如。这样的创作,在成人的现实生活的逻辑中,或许显得不合理,但却可以是儿童艺术世界中的上品佳作,细细品味,趣味别致!——如若品味这些作品的读者也能将自己“变了儿童”,想必更易为这纯情美趣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