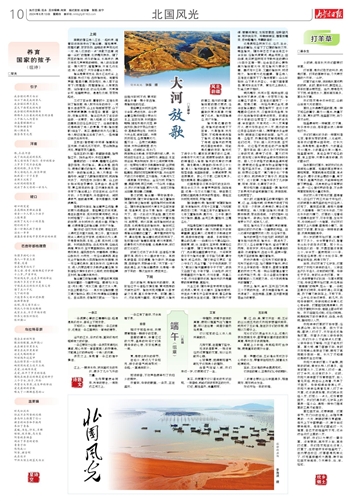小时候,每年秋天我们都要打羊草。
打羊草,是我们老家的叫法,就是打草。打来的草晾干后,冬天喂家里的六只羊、一头驴。
打草不能太早,须到晚秋草成熟的时候。此时,草籽长成,飘落地上,来年牧草会更茂密。当然,要是老天不下雨,或者雨水少,草籽再好再多,草也长不高。
我们老家是半农半牧区,山前山后有大片的草场。
草场上长得最茂盛的草,是一种不知名的蒿子,高约40厘米,质量不怎么样,夏秋时节,牲畜都不吃,到冬季才会吃。
牲畜最爱吃一种碱草,它不高,叶子绿中泛白,每年都会被人早早地打光。
我们打得比较多的一种草叫猪毛菜,春季发芽时很嫩,人也能吃,每年我们都要采回来吃。它长大后,浑身是刺,呈半圆形,大的直径约40厘米,小的直径也有20厘米,牲畜都爱吃。其他各种不知名的草,有上百种,只要长得足够高,我们都会打。
除去草场打草外,有时我们也去田间地头割草。地里的草主要有水稗和莠草。莠草就是狗尾巴草,有点像谷子,穗子没有谷穗的分量,弯不下身子,趾高气扬的,只能早早地被割下喂牲畜。沉甸甸的谷子弯腰低头,像一位心智成熟的老者,不会像莠草那样既无分量还张扬。
我们家从来不敢先打草,都是看别人已经打了两三天后才开始打。这时候草长得茂盛的地方已经被人打完了。高而密的草,得用大扇镰打,大扇镰是一种刀片长长的、刀杆也长长的大镰刀。打草的人站着将大扇镰夹在腋下,双手紧握,左右开弓,片刻就会打一大堆草。我们家打草用不上大扇镰,都是用小镰刀。刚刚打下的草,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清香,我常常陶醉其中。
我6岁时便开始打草,比镰刀高不了多少。爷爷带着我们,推着木头轮子的车去打草。那个木头车和古代的一样,方圆百里没有第二个,爷爷家一直使用到1970年。我现在经常想,那个木轮子车,要是留到现在,就是文物了。
后来,我们家有了毛驴车,打草就成了我和大弟弟的活儿。父亲在生产队干活儿,没有时间打草。母亲忙于家务,有时也会去打草。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找到一处草木葳蕤之地,母亲正要开始打草,听见身后“刷刷刷”的响声,扭头一看,一条蛇正朝我们爬来,母亲吓得心突突直跳,扔下镰刀跑到车上,不敢下来,一上午也没缓过神来。前几天,我和母亲聊天,母亲说起这件事儿还心有余悸。打草碰见蛇是常事儿,我们老家管蛇叫长虫,谁碰上都会吓够呛。我不但碰见过蛇,还捡过蛇蜕,就是蛇蜕下的干燥表皮,白色,半透明,据说可以入药。
我和弟弟打草时不怕辛苦,经常满山转,到处找草。因为下手晚,都被人打过了,只好在边边角角打草。我曾多次向父亲母亲抗议,我们为什么不能早点儿打草。父亲母亲也不解释,反正不能先打草。草太矮,镰刀都割不到,有时只好用锄头连根往下耪,耪完了再用耙子搂到一起。长大了才知道这是破坏生态环境。
我和大弟弟打草从不偷懒,同样的时间,肯定比别人打得多。但有时草太少,又被别人打过一遍,打了半天,也没有打多少。这时,我和大弟弟都不好意思回家,怕人看见笑话,就在山上待着,天黑了才回家。母亲知道后非常心疼。我和大弟弟经常看见有人打了半天草,还没装满车厢,我们就会笑话人家,打那么一点儿,还好意思回家。我们打得多时,毛驴车上的草像一座小山,得用一种专门捆绑草的工具才能捆紧。
草拉回家后,还要晾晒。打草季节,家门口的空地上,会摊开厚厚的一大片,晾晒时要反复翻腾,每天上下午都要翻一次,晾干后还要垛起来。每年我们都能打一大堆草,自己家的牲畜吃不完,还会送给没打上草的人家。
那时,我们以为要打一辈子草。没有想到,离开家乡后,再未打过草。我们老家现在也没有人打草了,庄稼秸秆足够牲畜吃了。在内蒙古牧区,打草都是机械化了,打完直接圈成大圆捆,晾干后拉回家垛起来,冬天喂牛、马、羊、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