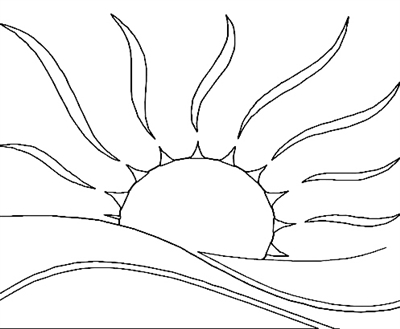这是一片面积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世隔绝、人迹罕至,没有明显的方位标志,也没有任何一块能够表明身份的石碑,那是充满未知的土地。
相比于草原和森林,戈壁的神秘感更强,无论处在哪个方位,都给人一种山高水远、难以抵达的感觉,人们说起它时,神色间总带着一丝向往、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和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
尽管是冬季,戈壁的颜色却并不单调,无数砾石珠宝一样散落在这片被人遗忘的土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它们是久经考验的勇士,更是历经万难的行者,更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不会消弭的戈壁的蓑衣。额济纳旗黑鹰山附近的戈壁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五色戈壁,白、黄、红、灰、黑的大片土地起起伏伏,令人惊叹。其中以黑戈壁声名最为显赫。原因是那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棱角分明、乌黑油亮的石头,有煤炭一样的颜色,却又比煤炭更加尖锐。
戈壁昼夜温差大,到了夜晚,白日里被晒得滚烫的石头表面会有水珠凝结,这些水溶解并带出了石头里的铁和锰,经过千年的演变后,矿物质沉淀在石头
表面,并逐渐将石头包裹起来,形成了一层颜色奇异的“包浆”。
如此一折射,就又找到了戈壁人性格的底色:为何他们面对困境仍能怡然自得?为何他们遭遇了天灾人祸后依然笑得灿烂?为何他们日复一日地放牧、游走,岁岁年年与牲畜相伴却仍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自得其乐呢?那是因为博大如母亲般的戈壁早就为他们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无论过往如何喧嚣,最终都要归于平静,一切生命、一切存在都如此,唯有贞静才能长久存在。
说起戈壁,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可堪与走西口、闯关东相提并论的新名词:趟戈壁,特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甘肃逃荒到周边各省市的大型人口迁移现象。我的爷爷就是在那个阶段从甘肃来到阿拉善的,这片隐秘而伟大的土地毫不吝啬地接纳了爷爷奶奶和我的父亲,然后才有了后辈们的枝繁叶茂和李氏家族的源远流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戈壁对我有救命之恩,它虽夏热冬冷、干旱少雨、方位难辨,但在半个世纪前,它为我的祖辈辟出了一条生的道路,让李氏家族的后辈不至在风雨中飘零离散。
后来,爷爷半生都没有离开戈壁,他放下锄头拿起了牧鞭,将一群牲畜侍弄得红红火火,也将戈壁的每一寸土地都印在了自己的血脉里。他甚至比土生土长的戈壁人还要了解戈壁,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那些野生动物、家养牲畜的习性和特点,以及节气、时令的变化,他都了然于胸,仿佛他生来就是戈壁的孩子。在戈壁深处,还有许许多多像爷爷一样的人,他们是同一把火的种子,星火一样在戈壁上燃起燎原之势,无论站在哪里呼喊一声,他们的回应都山呼海啸般响起,是他们,最终激活了这隐秘而伟大的角落。
中国的各式地形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戈壁。事实上,戈壁中留存的古镇遗址和散落的文明随处可见,它们比许多闻名天下的城镇更具有研究和游览价值。走进这些古城,四下安静无人打扰,滚滚烟尘里,沉寂了百余年的文明骤然重现,多年前那种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景象令人热血沸腾,无论站在哪个时间节点回望,它们都是当之无愧的瀚海遗珠。它们处在隐秘的角落,却又饱含伟大的力量,这与戈壁的影响力恰好相合。
许多人从戈壁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戈壁广阔与隐秘并存的特质给予了他们心无旁骛和专注的力量。这份特质也给予了我力量,它使我历经艰辛却仍无所畏惧,无论走到哪里,它都将是我心中那个永远隐秘而伟大的精神家园。文/李 娜